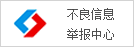此次听证会聚焦两项极具争议性的提案。其一,计划对进口自中国的岸桥(STS)起重机加征高达100%的关税;其二,要对集装箱、底盘及其零部件等货物装卸设备征收20%至100%不等的阶梯式关税。
听证会上,美国港口协会(AAPA)、众多航运企业以及行业代表纷纷强烈抗议。然而,由USTR牵头、多部门组成的美国政府小组,却对业界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,依旧坚持推进相关政策,还驳回了业界提出的“分阶段征收港口费”以及“对外国建造汽车运输船收费”等建议。

政策核心争议:本土产能匮乏与成本飙升
岸桥起重机关税冲击港口基建美国港务局协会(AAPA)首席执行官加里·戴维斯指出,自20世纪80年代起,美国本土就已没有STS起重机制造商。目前,全球市场70%的份额被中国企业——中集振华(ZMPC)牢牢占据。剩余的市场份额则由日本三井E&S、芬兰科尼(Konecranes)和德国利勃海尔(Liebherr)三家企业瓜分,但它们的年产量总和还不到全球需求的15%。
休斯敦港首席执行官查理·詹金斯透露,该港在2024年与中国签订了一份采购8台起重机的合同,总价为1.12亿美元。但由于关税政策具有追溯适用性,最终成本将飙升至3.024亿美元。这一成本的暴涨,直接威胁到港口的扩建计划,还可能导致数千个就业岗位面临危机。
AAPA估算,一旦关税政策落地实施,全美港口将额外承担70亿美元的成本,而且美国本土的产能根本无法填补这一缺口。
汽车运输船收费遭航运业抵制
美国航运商会(CSA)会长凯西·梅特卡夫严厉批评,对外国建造的汽车运输船按运力统一收费的做法“既武断又违背常理”,这一举措极有可能推高汽车物流成本,进而扰乱整个供应链。世界航运理事会(WSC)也发出警告,称此举“远远超出了USTR的法定权限”,航运公司为了转嫁成本,必然会通过附加费的方式,最终这些成本都将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。
政策逻辑矛盾:保护主义与产业现实脱节
本土造船业复兴无望
美国商用造船产能仅为中国的6.3%,而且劳动力断层问题十分严重。据预测,到2030年前,27%的焊接工、34%的舾装工将退休,而高校船舶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数量有限,难以填补这些岗位空缺。
即便《美国船舶法案》强制要求10%的输美货物由美籍船舶运输,但美籍船舶的单箱成本仍比中国高出83%。这种结构性缺陷,绝不是通过短期政策就能弥补的。
规则对冲风险
中国主导的《联合国国际船舶司法出售公约》将于2026年生效,这一公约可能会削弱美国通过海事管辖权实施制裁的能力,进一步动摇了相关政策的基础。
行业应对与全球影响

航运企业调整策略
为了规避相关费用,达飞等航运公司计划对航线进行优化,减少中国建造船舶停靠美国港口的频次。全球供应链连锁反应
若该政策落地实施,大型航运公司如地中海航运(MSC)和马士基(Maersk)将面临巨额成本压力。这两家公司现有船队中约25%为中国建造,而在建订单对中国建造船舶的依赖度更高,达到了70% - 90%。分析机构预测,亚美航线运费率可能会年均上涨9.2%,这将进一步加剧全球通胀压力。
政策背后的政治博弈
USTR声称此举是为了“平衡中国在全球航运业的主导地位,保护美国经济安全”,但这种单边行动更多地被认为是为了服务选举政治。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强硬路线,试图通过关税议题来巩固“抗中”形象,却忽视了本土产业空心化以及盟友技术依赖等深层次矛盾。
正如AAPA所呼吁的,美国若想重建制造业竞争力,应该采取税收抵免等市场化激励政策,而不是以牺牲港口与消费者利益为代价,实施“惩罚性关税”。
此次听证会充分暴露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困境。一方面,美国无法扭转中国在全球航运业的领先地位;另一方面,又难以弥补国内产业的结构性短板。
如果该政策强行推进,极有可能引发全球供应链紊乱,最终对美国经济和地缘战略目标造成反噬。